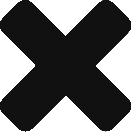上班之前,每天的工作是带小孩,时间相对自由,可以带着她去这里那里,差不多每天都要去Trader Joe’s逛一逛打发时间,看看出了什么新产品,带她去Target买东西,带她去公园,植物园,动物园。带完孩子之外的生活比较随性,想起来就去二手店,石头店,植物店,面包店逛一逛,也在Nextdoor上逛一逛,在路边闲逛时留意身边的事物,花鸟虫蘑菇房子。练琴的时间也会多一些,一周七天能练个四五次。因为时间相对自由,心境上会放松一些,也更有兴致去观察周边,做些记录。
上班的头两周特别忙,回到家再带完两个小时孩子之后脑子都是蒙的,有天下班带着孩子出门险些出了车祸,又一次晚上做完饭忘了关火,早晨家人起来发现食物已经烧焦碳化,还好是小火没引发什么火灾事故。过了这头两周之后又没那么忙碌了,每天竟还有几个小时的空闲,于是我也研究起了摸鱼之道,想着如何更有组织更有效率地上班摸鱼时提升自己,或是更加系统地发展自己的爱好,目前有以下一些想法:
1. 完成Cousera上的一门写作课并持续写作。
2. 完成之前花了30美元买的水彩画课,或是去了解下彩铅课
3. 继续学习编程。
4. 学印地语和韩语。
5. 考个房产经纪
6. 考个职业整理师
7. 看之前想看却一直没看的闲书
8. 学习缝纫
9. 研究烹饪
九月底写作小组又重新恢复了见面,我在上班时间里摸鱼完成了本周的写作任务,小组见面时得到了很好的反馈,接下来准备更加积极地写作,最好能每天都写一点,不管是写日志还是写别的什么。
上班之后没有太多闲适的时间了,一切都要有规划和安排,虽然这不是我所习惯的生活方式,但经过两周的适应也很快调整过来了。现在的工作我不能说多么有趣,但有工作能学新东西并且有些收入总归是件好事。工作也强迫我让自己的生活变得有计划和规律起来,我几十年来都没怎么早起过,现在也是每天七点起床八点上班,晚上十点睡觉。
上班路上我也会留意一些有趣的事,算是给比较机械的上班生活里添一些乐子。有一天我前面有位爸爸骑着车载着女儿,女儿在后座,身体往右倾斜,伸出手够着摸路边的植物,这一幕算是那天上班路上的趣点。每天去办公楼要上一个大坡,是平凡生活里的小挑战,上班一个大坡要骑上去,回家也有一个大坡要骑上去,是否顺利蹬到顶则完全取决于那天的状态和心情。有时候下楼去洗手间,经过楼梯间的窗户,可以看到外面的森林,我会留意一个枝条上有多少叶子黄了,什么时候变的色。午饭间如果不那么困,也在楼边的林子里走了几次,多体验一下漫长冬天来临前最后的好天气。
进入了这种规律生活凡事规划的生活状态后,我也开始更积极地和朋友保持联系,约前同事或是系里的同学出来见面,参加妈妈小组的活动,和聊得来的妈妈单独约见,去参加朋友的小提琴音乐会。总之上班以来状态还是很好的,上班好过当全职妈妈好过念文科博士。希望这种良性的状态能持久一点,如果能把锻炼身体这件事提上日程那就更好了。